
小时候,我们把冬天叫做“熬冬”,一个“熬”字,体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与不屈。那时候,身体不好的老人,总是小心翼翼地窝在屋里,生怕一个小小的喷嚏就断送了性命;孩子们裹成了棉球,各种厚衣服往身上招呼,浑身上下只有眼睛露在外面,长长的睫毛上挂着哈气变成的霜。成年人除了照顾老小,还得为一家人每天的吃食奔忙。
入冬前的准备,最早进家门的其实是煤。大家都记得,买煤都是在秋天吧?秋天买煤要比冬天便宜不少,精打细算的人家都会选择提前购买。
我家买煤一般是在夏末秋初,这时候的煤站运来了新煤,虽说贵一些,可都是大个地块儿煤,烧起来特别好。坝上的夏末已经没有了灼灼烈日,变得清爽怡人。父母挑一个休息日,把家中的煤房打扫出来。那时候,县城的人们都住在平房里,有个小院子,小院子里有正房小房,小房中有一间是煤房。
煤房长年累月的灰头土脸,一年唯一被打扫的机会就是在新煤进入之前。父母戴着口罩和布帽子,穿着劳动布衣服,先洒些水,然后两把扫帚上下飞舞,扫出一堆堆的煤渣子。煤渣子不能浪费,掺和上泥水做成蜂窝煤,也能烧。清扫煤房,其实是一种重新规划,毕竟煤房里除了煤以外还有好多杂物,把它们归置好,用砖头圈出煤槽,此活完成。

买煤不易,若是煤站有熟人,能挑一挑堆儿,没有的话只能随即拉,在我看来没啥区别,可在万事需求人,有人好办事的心理作用下,人们都会找找熟人。买煤是按吨计算,往家运煤则要雇佣畜力车。
雇用畜力车是当时很多出身农村的人们达成的共识。一来拖拉机比较少,费用高,二来畜力车多是周边村子里的农民利用收割庄稼前的间隙赚点外快,拉活时闲言碎语少。
拉煤的皆是四五十岁的大叔,他们一天只接两趟活,上下午各一趟。不管你买多少煤,他拉几回,都是一次性计费。煤拉回家,你帮忙也可,不帮亦没事,他负责卸车,把煤搬进煤房。作为雇佣者,无论中午下午,要管一顿饭。如今的人们可能理解不了,觉着我付了钱为什么还要管饭。那个年头的人们还保持着一丝淳朴的观念,干活吃饭,天经地义。当然,也有吝啬的人家不管,但不是主流。
拉煤大叔卸完煤,主家端来热水肥皂让他清洗手脸脖子。别看大叔们是乡下人,可十分讲究,自己备着小扫把毛巾,先扫衣服上的渣,再掸灰土。收拾好,他们脱下外衣放在院子里,进屋吃饭。饭很实在,多数是羊肉蘑菇汤蘸莜面,有一两个量大的下酒菜,酒管够,饭管饱。若是中午,大叔们喝得很节制,因为还寻思着下午再接趟活,若是下午,大叔们敞开量,喝至微醺,赶着车摇摇晃晃地哼着小曲,在夕阳下向村子愈走愈远。

解决了取暖问题,入冬的准备算是有了基础,人们心里有了底,剩下的要解决的是吃食,也就是准备过冬的蔬菜。
过冬蔬菜首选大白菜,储存时间长,不怕冷冻。每到秋末,四周村子里的菜农们齐聚县城,售卖自家白菜。人们谈好价格,他们负责运到家里,把白菜卸在院子里,接着奔向下一家。
院子里的白菜,有的入小房,有的下地窖,搬运时候全家总动员,嘻嘻哈哈一会功夫便把白菜整整齐齐的码好。码白菜也有学问,要分缝隙码,这样不至于让它们粘在一起变黏。
白菜入库,紧接着是腌制咸菜。咸菜是坝上人家过冬的法宝,需要腌制的种类很多,什么芥菜疙瘩、雪里蕻是基本操作,大萝卜、洋姜、地葫芦、辣椒、韭菜、芫荽等用小瓶子小坛子来腌,瓶瓶罐罐摆一地。最麻烦的是蒸西红柿酱,清洗葡萄糖瓶子、蒸西红柿、扒皮、切块儿、塞瓶、拔空气,又是一场全家总动员。
我们这里人们爱吃粉条。冬天来块白玉般的豆腐,放上大白菜、肥肉片子,在炉子上咕嘟,最后把粉条放进去,出锅撒点胡椒粉,吃起来浑身通泰。粉条是土豆制成,县城里的人们会做,但没有做的条件。这东西也不用买,老家的人们会集中几天时间制粉,粉条做成椭圆形的圆盘状,一袋子一袋子的给城里亲戚送过来,能吃一个冬天。吃不了也不怕,这东西随时能买上,价钱也不贵。
有的人家在入冬前还要晾晒些干菜,以豆角为主。豆角剪成丝儿,放在院子的水泥地上晒干,线绳子扎成捆,挂在小房梁上,到了冬天,算是白菜豆腐粉条之外的调剂。

家里有老人的,闲着没事,会在入冬前拆洗棉被和棉衣裤,或者做些新的棉衣。老人们做棉衣,不着急,几个人凑在一起,盘腿儿坐在炕上,边聊天边做。棉衣里的棉花是按斤算,比如棉裤,人们说起来是做了条几斤的棉裤。
在那个信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、勤劳致富的年月,入冬前的准备是忙碌而幸福的。全家人亲手把点滴汇聚,使得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温度和爱。零下三十度的冬天,正因为有了这些,才让人们无惧寒冷,热情洋溢地生活。或许,如今不需要我们准备的冬天,总是寡淡无味,少的正是那些自信乐观的脸吧。
转载请注明来自江苏龙湖电气科技有限公司,本文标题:《新奥彩资料免费最新版,解答落实:散文:入冬前的准备 》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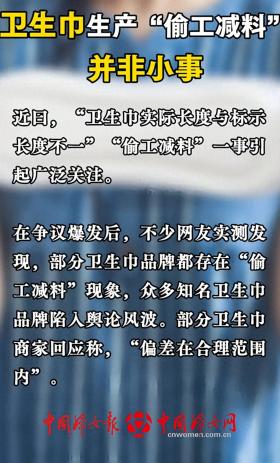

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
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